这个世界的随机性
前记:
This is a placeholder for a new blog, which is expected to be finished by the end of 2025. I will talk about the take-aways from graduate school, the randomness - both mathematically and philosophically I think about the world, and my impression on NYC as a new comer.
05/03/2025
全文约 5,000 字,预计阅读时长 13 分钟。本文经过AI润色。
千思万绪,从何说起。
在曼哈顿的高楼与车流之间,我有时会想起在俄亥俄的最后一天,把车开去卖掉的那天。开在midwest的高速公路上,窗外是六年如一日单调的风景。想到我的小破车要离开我,我心里感到些不舍。我把车牌卸下收起来,带到纽约的公寓,静静放在角落里。
博士毕业了,人生的重要一章合上。物理是我人生中十余年的主题,拥有一个博士学位这件事从来不是个惊喜。但有些事我几乎忘记了——答辩那天,国内的发小凌晨爬起来听天书。过后她说虽然完全没听懂,但想起来高一的时候在学校长廊上我跟她说以后要学物理,有幸十几年后见证了这话兑现。人在生活,与人建立联系,就像一路将自己的灵魂碎片寄予他人,那些碎片收藏者们带着各自的记忆潜伏着,等待某个时刻温柔归还。
我想起来我这里也有一份灵魂碎片——我后来学物理,有一半的原因要来自于高中时很喜欢物理课和物理老师,我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提到了这回事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high school physics teacher Mr. Luo - also thanks to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the small perturbations he seeded on our blackboard expand to a few solid scientific research I have done in this thesis.
但遇到一位天才导师这件事,对我而言完全是个意外。我刚到OSU时,本打算做天体粒子物理或者弦论。打开物理系的教授列表研究时,注意到一位做宇宙学的教授——低调但履历耀眼:引用2w+;13岁时成为了美国最年轻的IPhO金牌得主;智商有两百多;14岁入读加州理工,22岁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24岁便在加州理工任教,后来与同样杰出的暗物质研究者、他的夫人一同来到 OSU。我感到很好奇,到哥伦布以后没几天,我很快摸进了他的办公室。第一次交谈,我觉得他讲话很慢,平实谦和,和我想象中那种锋利的天才气质很不一样。说着磕磕绊绊英语的我,也觉得自己没那么突兀。我后来读到杨振宁到芝加哥读博和泰勒第一次见面,泰勒问他氢原子的基态波函数是什么,他答得很好,于是成为了泰勒的学生。而那天我很老实地说,我学过些东西,但都懂得很浅,我感兴趣你在做什么,也许我可以多来听听,Chris说好。
只要稍懂一点数学物理的人,和 Chris 交谈片刻便能感受到他的非凡。我常常同时进行几个project,在meeting里从一个跳到另一个,随口抛出开放性问题,他总能从容解答——不翻书、不查资料,徒手推演出一整板公式,给出定量的回答。回去查文献时,才发现他那些看似随意的推导,与paper上的结果分毫不差,这才意识到他或许真的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记得一次聚餐,话题转到即将到来的日全食。有人随口问:“如果逆着地球自转方向前进,要多快的速度才能一直看到日全食?” Chris稍一沉吟,几秒钟就报出答案,接着又花几分钟解释建模过程和数量级估算。当一个博士生在研究中遇到许多难题和挑战,推开隔壁办公室的门就能找到Chris这样数理GPT般的老师,常感到身后的支持有如泰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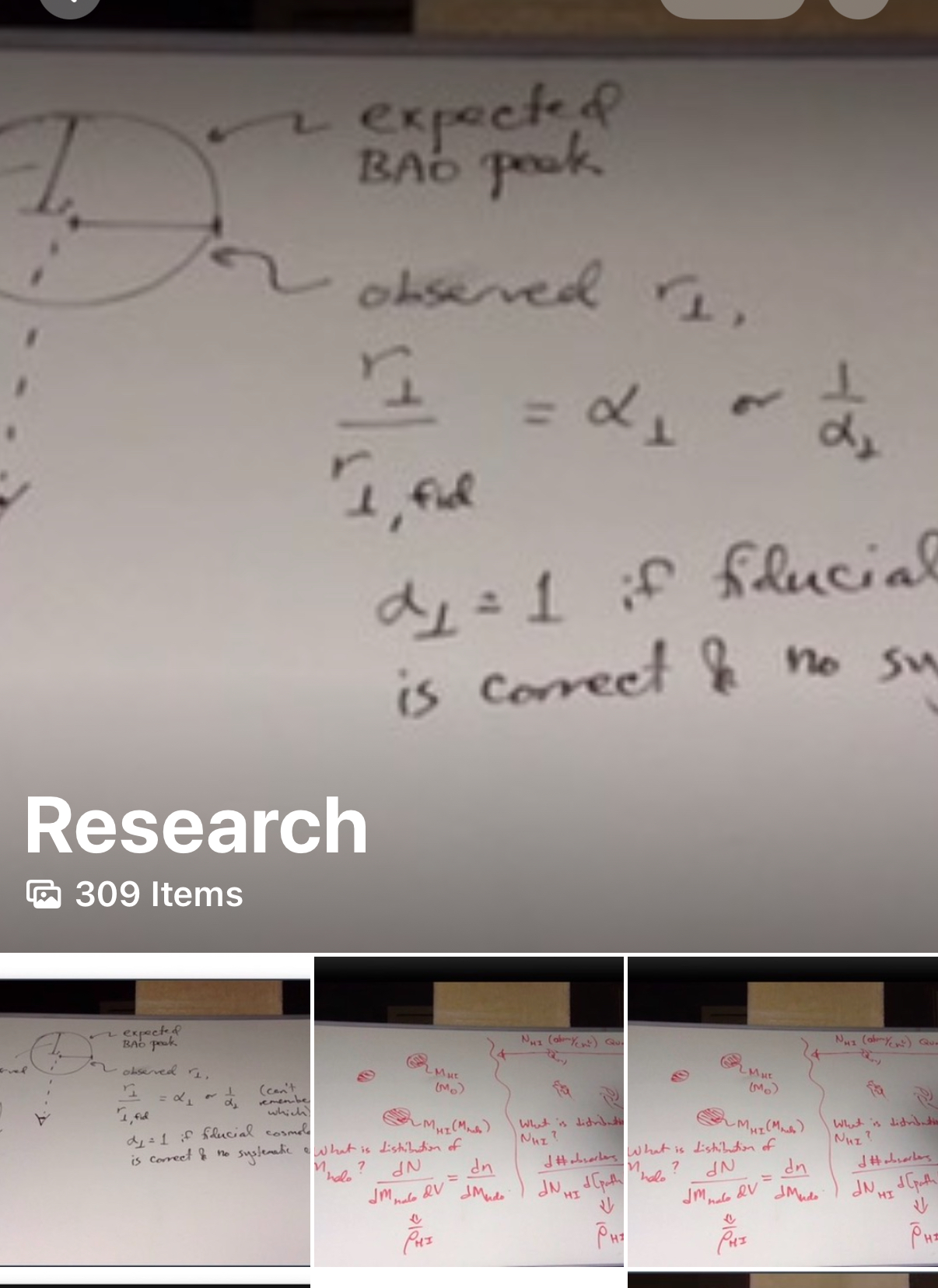
和Chris共事一段时间后,我逐渐发现——智商不通过师生关系传播。虽然心里有些失望,但也开始思考些以前从没想过的东西。Chris也是我遇到过最耐心的老师。他乐于讨论任何数学或物理问题,愿意花大量时间和学生待在一起,从不评判问题的大小与高低。如果一种方式没能讲明白,他会立刻换个角度再解释。和他讨论时,我从不担心问题太幼稚,也不会觉得被凝视,更从未感到他是我的某个上级。有时候尽管讨论的知识很高深,感觉却仿佛平常的一天回到家,邻居小伙伴向我分享了核聚变技术。这些不平常的体验,让我常常会想——为什么一个天赋卓绝的人,能够如此平易近人?
让我来谈谈生而为人的随机性吧。一个人出生的族群、家庭、时代、智力、天赋等种种分布,本就像骰子落下的数字,不可选择。人与人,也如同硬币的正反面、骰子的六个面,或概率分布中的不同采样——看似各异,却同源而生。如果我因为落在概率的一端,恰好幸运地因为理工科上的天赋而在世上立足,那必定有人不幸地因为才华缺乏相应的土壤而被埋没了。天赋是gift,值得感恩,值得珍惜,而除了独善其身之外,用自己的gift来帮助别人或世界变得更好,是回报这份概率的馈赠最温柔、真诚的方式。他人、世界与自我,原本同源一体。我不知道年少即名动四方的Chris是什么时候明白这一点,并始终如一地践行,而我是在认识他许久之后,才顿然领悟。
我从Chris身上学到的另一点,是关于做研究的信念。在我提出的无数疑问与他的回答之间,最令我难忘的,是每当我问他:“XXX有没有办法算出来?”他总会微笑着说:“There is always a way.” 渐渐地,我体会到,人类在拓展知识边界的过程中,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障碍,但也会不断地上下求索、创造方法,去巧妙化解难题,探索未知。这些不断尝试、反复推演的过程,就是research。对研究者来说,既选择了踏入无人涉足的领域,就意味着要以纯熟的技巧、平和的心态和无畏的精神去面对未知。这种信念,不仅是科学进步的基石,更是一种闪光的力量。它跨越学科,超越科学本身,也悄然渗入我的人生——在人生的难题和低谷面前,支撑我穿越暴风雨,成长与蜕变的,也是这样的信念。
后来我决定离开学术界时,与Chris有过一场艰难的对话。他不曾试图影响我的选择,只是为我们曾经努力和憧憬的学术前景悄然殒落而感到难过,却仍然给予我最充分的尊重与支持。面对史上最难的找工季,我有一年多时间淡出了科研,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业界所需的知识、准备面试。我知道,许多导师都不会容忍学生这样的“分心”,而Chris告诉我:你已经做得足够多、足够好,只需要安心去找工作就好。我在找quant职位过程中,遇到稀奇古怪的数学、统计问题,有时候自己实在想不明白,也去跟Chris讨论,他依然有竞赛金牌得主的风范,常常砍瓜切菜一般地解答了。
现在我离开物理,进入这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了。而渐渐明白——善良也许是一种特质,却越来越多地是一种选择。有时听朋友抱怨,像川普和马斯克这样糟糕的人,不仅没有因为他们的道德低下而受罚,反而愈加风光,“做个好人”是否是件无用的事。我想,在这世界上,如果人选择善良,得足够强大。你得比在同样环境下的不善良的人强大,得有对挫败和委屈悉数收下的心胸,要有在现实中而非仅是理想里战斗的坚韧和勇气。如果我们要做一种生活的选择,既不加入这世上的浊流,亦不遁世而去孤远天外,而是做一个为彼此创造空间和战斗的人——那就得有勇气,去准备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如此的旅途,若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中偶然遇见,认出彼此的脸,道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吧。
扪心自问我有没有一个瞬间爱过俄亥俄,应该可以说没有。我不怀念那里无聊的景象与乏味的生活,却时常想念日复一日钻进办公室一待就是一整天的单纯和热忱,想念与老师简单朴实的相处,想念那份有万钧之力的平常。我想在中西部单调的平原与尘世之上,还有我们用对科学的纯粹热爱和对于平等的信仰所构建的精神的乌托邦,是我自由生长和怀念的故乡。人在生活,与人建立联系,就像是一路收集着他们的灵魂碎片,它们潜伏着,直到某个时刻,你遭遇了这世上难渡的困顿和苦厄。这时闭上眼睛,想起平常的一天,念一句元神归位,那些灵魂碎片会从四面八方穿山越岭乘风而来,将人温柔地托住。
遇到Chris,是我人生中另一个莫大的幸运。我不再渴望自己像他一样有超人的天赋,而常常希望自己爱别人时,也能像他一样看见、接纳与支持。他从我远望见的那座高山,变成平常,然后他的修行变成我的修行,他的善良也变成我的。
来到纽约对我来说不是个偶然,而是一个决定。心理学上讲,在重大的生活选择面前,“decide”与“slide”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主动去决定的人,往往比顺势滑入某个结果的人,对生活拥有更深的满足感。我那时挣扎了许久,最终没有滑向一个看似理所当然的,留在学术界做博后的选择。我接受了阵痛,决定重新出发,希望找到一份工作把生活带到纽约。来到纽约9个月了,我感到喜欢这座城市,她给了我许多我想要的,还没有的,她给我要去找到的勇气。我看到王菲曾在一段采访里说:
我很喜欢纽约的其实,我觉得那的人,我在大街上看到他们走路的神态,和他们的那个感觉,我觉得他们充满自信,不管他是什么样子,奇形怪状,他都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那个给我一个灵感,我觉得我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纽约包容了所有像我一样奇奇怪怪的人,我想不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建筑多么神奇,而是不论你有多么奇怪,你都能在这里找到和你一样奇怪的人。我在这里很快拥有了一些友谊,下班之后聚在喜欢的川菜馆吃辣,几个人开始叽叽喳喳,直到天色渐晚各自回家。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享受过这样温暖平常的陪伴了。我遇到形形色色精彩的人,常常能看到世界顶级的艺术展,去公园散步,听脱口秀,看钟爱的老电影,玩好玩的桌游,开始打网球,做咖啡时拉一朵花。有天走在下东区的街上,我感到被温柔的光轻轻包裹住。我发现如今如果想要为自己保留一些安静独处的时间,需要小心地保护自己的日程不被各色精彩的活动悄悄占满。Ohio生,Ohio长的小猫霸天和我一起经历了来到大纽约的迁徙,她比五年前我刚认识她时外向了一些,还是吃得不多,喜欢在窗边上找地方趴下来,看窗外树影摇晃。
很久以前,读木心的诗《杰克逊高地》,当时觉得句子动人,却不知道诗名来自哪里。直到搬来纽约后的某天,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正是住在这个Jackson Heights,而地图上往北走一点就能看到木心故居。
杰克逊高地
木心
五月将尽
连日强光普照
一路一路树荫
呆滞到傍晚
红胸鸟在电线上啭鸣
天色舒齐地暗下来
那是慢慢地,很慢
绿叶藂间的白屋
夕阳射亮玻璃
草坪湿透,还在洒
蓝紫鸢尾花一味梦幻
都相约暗下,暗下
清晰 和蔼 委婉
不知原谅什么
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对于离开物理这件事,我心里依然有些地方未曾释怀。来到纽约,融入这座城市漂泊的人群,我很快发现自己遭遇了身份认同危机。每当向别人介绍自己时,说“我做金融”或者“我写代码”,总觉得有些奇怪。对在美的中国人而言,这些都是最普通的标签,但在我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是学物理的”。我渐渐想明白这事——人生并不会完全按照我们年少时的设想展开,这并不奇怪。过去的一切将我带到现在,时间与世界就这样流动,就如世间的缘分一样。我常常觉得,物理依然流动在我的血液里,塑造我思考问题的方式。教育,是那些忘记了一切细节之后,仍然沉淀在人身上的东西。对我来说它也许并不必以某种物质形态存在,而我依然永远是个“学物理的”。我没有为物理的发展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但它在很长的时光里陪伴了孤独的我,在无数方面塑造了如今的我。我接受了自己的幸运,也学会了对缘分的流动感到释然。
我现在更经常思考世界和自己了,我觉得我比过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自己了,同时发现——人在认识和发现自己的旅程上也许永远不会有一个终点。我最近关于世界的一个迷思是——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模拟。那些无处不在的随机性,无数事件背后概率的本质,都让我觉得,如果有天算力强大到能够模拟世界本身,也不必惊讶。而一旦陷入对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追问,人便早晚会与尼采相逢。当我思考“如果世界是个模拟”会如何改变我的世界观与行为时,我了解到尼采提出的“永恒轮回”——
你是否愿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你此刻的人生?
尼采说,人应该活出你愿意永恒重复的一生。
尼采还说“上帝已死”——
如果这世上没有神,也没有终极意义,我们为何而活?
他说要去主动面对虚无,创造自己的意义。我由衷接受。
比起四年前的我,如今最大的转变,是我更愿意在真实世界的反馈中去成长了。过去我常以为,我已经想得足够多,对自己也算坦诚,但直到以人为镜,才惊觉身上仍有许多盲区,还有无数可以努力的地方。过去我总是隐隐觉得,自己不够释然,朋友却认真地批评我:不是的,你还不够坦率,也不够勇敢。你要更勇敢。那之后我突然看到自己蜷缩在黑暗中的内在小孩,才发现多年来我用一层层铠甲把她保护住,却从没有真正让她长大。我还在种我的树,种十年前没有种的树,种奇奇怪怪的树。我有个朋友,50岁了还在种树,我时而听到她说:“天下谁人不识君”。我依然在读黑塞,这一年多,我常常想起他的话,用自己眼中的世界去察觉自己——
别人眼中的你,不是真的你。你眼中的自己,也不是真的你。你眼中的别人,才是真正的你。
我发现夏天结束时总是伴随着许多故事的发生和告别,我最好的回忆都在夏天了。夏夜的晚风中,我会对着我的那些灵魂碎片发呆。它们像星辰一样,静静悬在空中,每一片都映出我曾经的心动和失落。在这充满随机性的世界上,北冰洋和尼罗河的水终会再相逢吗?也许我们并不总能等到再饮一盏茶,将碎片归还的那刻。而所有的踪迹已在这世间沉淀交织,如同原初时代的光还在宇宙深处不知疲倦地奔流,使我时常想念,时常叹息。
08/20/2025 @ New York